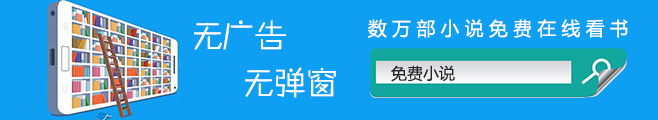两京十五日 第4节
想到自己父亲,吴定缘突然意识到,如今东水关闹出这么大的乱子,吴不平身为应天府总捕头,肯定也会被牵连进去。万一这案子没破了,以官府的秉性,说不定会把他推出来顶缸,谁让你负责南京地面的平靖呢?
想到这里,吴定缘叹了口气:“好吧,好吧,我说还不成吗?”
接下来,吴定缘把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讲给了于谦听,如何看守扇骨台,如何看到宝船上的人影,如何救下太子,如何碰到那两个怀有杀意的卫所旗兵,自己又是如何改变主意把人犯押来锦衣卫。
一番话听完,于谦对这个惫懒捕吏倒真是刮目相看。这家伙的谈吐虽然粗鄙,但分析起事端来,却简洁精准,切中肯綮,就是积年老吏也未必有这种见识。那个小旗嘴里的“蔑篙子”,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精明人。
他极其鄙夷吴定缘一遇到危险便推卸责任的做法,但很认同其判断——这个幕后策划者显然是要把太子和南京官场一网打尽,其野心之大、规划之周密、手段之狠辣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
不幸中的万幸是,太子奇迹般地得以幸免,吴定缘又临时起意,将其扭送锦衣卫。这一连串意外,神仙也没法事先预料,更别说那些炸船的反贼了。
也就是说,太子至少现在很安全。
吴定缘见于谦眉角一下子松弛下来,便猜到了他的心思,不由得嘿嘿一笑:“你说,他们花了这么多心思炸船,难道只是为了听个响动?”
“什么?”
“今天,可还没过完呢。”吴定缘抬起眼皮,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。
于谦眼皮猛然一跳。
糟了,那个老千户跑去东水关码头打探消息,万一到处表功说收容了太子,难保不会被反贼的耳目侦知。一想到这个,于谦顾不上向吴定缘说明,转身迅速离开内狱,蹬蹬快步朝前院走去。不管这种可能有多少,必须得让锦衣卫提前做好防范。
可当于谦回到前院时,却发现圈椅上空无一人,太子不见了,附近那几位副千户也没了踪影。于谦大惊,抓着旁边一个留守的小旗问怎么回事?
小旗倒老实,直接全说了出来。原来在于谦离开不久,码头那边的老千户便传回消息,一好一坏:坏消息是,襄城伯受了重伤,他身在码头最前,受冲击最强烈,一时还未醒转过来;好消息是,三保太监侥幸无事。在爆炸前一瞬,他的大氅半边脱落,几个侍从正手忙脚乱地挡在身前摆弄卡扣,替他挡住了大半冲击。
三保太监见惯了大风浪,临危不惧,坐镇码头指挥。在他的调度下,东水关与南京诸衙署已逐渐恢复了秩序,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着。恰好老千户跑过来禀明太子下落,郑和一听,亲自赶来迎候,刚刚把太子接走。
那个老千户耍了点手段,接走太子时,故意没通知在内狱的于谦。
于谦听说接走太子的是郑和,不由得长出一口气。郑和是永乐老臣,其人忠直耿介,兼有韬略,几次下西洋的壮举攒下偌大声望。只要有他这尊山岳镇着,南京城乱不起来。
不过眼下尚不是松懈之时。于谦认为,吴定缘遭遇两名旗兵袭击这条线索很重要,必须尽快让高层知道才行,便讨来一副纸笔。
他的笔法流畅,转瞬就写满了一页工整的台阁体。信中警告太子与三保太监,南京城里还有敌人未除,要尽快彻查,不可轻忽。信末还不忘提了一句吴定缘的冤枉之情,生怕贵人们事情一多给忘了。
写完以后,于谦吹一吹淋漓的墨汁,四方叠好揣在怀里,举步匆匆出门。
此时外头崇礼大街上还是一片混乱景象,两侧街面的旗幌下、沟渠旁、树荫下都站满了人,个个面色惶恐。先前大家只是听到巨响,不明所以,现在宝船被炸的消息已从东水关码头扩散开来,这在南京居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甚至已有零星百姓卷起包袱,扶老携幼,打算出城避难去了。
于谦不知道太子与三保太监如今身在何处,但以情势推断,他们一定会先行返回南京守备衙门,那里是整个留都最安全的地方。
南京守备衙门位于皇城西南角,无论队伍从哪条路线行进,皇城西侧的西安门都是必经之路。他只消从崇礼街转到大通街,一路向北穿过西皇城根南街,赶到西安门外的玄津桥,就一定能截住队伍。
于谦略扶一下幞头,把腰间的乌角带提了提,举步从惶恐不安的人群快步穿过去,钻进一条小巷子里。他来南京已有数年,城内地理轻车熟路,知道哪里有捷径可走。不消两炷香的功夫,于谦已经跑到了西皇城根南街的中段。
他一踏上街面,伸着脖子朝北边看去,只见烟尘滚滚,前方一百多步开外,一支队伍正匆匆移动着。
这队伍的构成颇为驳杂,里面既有顶盔贯甲的守备衙门亲兵,也有一身短衫的勋贵府家丁,有人腰悬弓箭,还有人手擎金瓜,乱七八糟不成章法。不用问,这一定是护送太子的队伍。东水关爆炸波及人数太多,只能临时拼凑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手。
队伍之中,最醒目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青海大马,上头的骑士头顶高丽冠、身披猩红大氅,无论马背如何起伏,双肩始终稳稳不动。在他身边,还有一抬黄绸阔轿,抬杠的却不是轿夫,而是几个身披彩肩的号手。
那个在马上的高大身影,想必就是三保太监郑和;而他旁边的阔轿之内,只可能是当今太子朱瞻基。
那支队伍移动速度很快,眼下队首已越过桥头的守桥石狮,即将踏上玄津桥面。于谦略喘了口气,加快速度追了上去。
玄津桥是一座三眼白石拱桥,两端斜坡,中间高拱如山。它横跨秦淮内河,对面即是西安门。当年南京还是京城时,百官每日出入皇城,都必须通过玄津桥从西安门入皇城,一度是南京最繁盛的路口。
这玄津桥最大的特点,就是桥两头各卡着两尊石狮,说是镇岁辟邪之用,其实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。它们把石桥入口分成三条狭窄的通道,防止太多车马一次涌上桥面。
因此当这支队伍走到桥头,不得不让队形稍做变换。簇拥在前方的护卫让开路面,先让三保太监和那顶阔轿从两座石狮中间的狭窄通道走过,他们再从两侧过道跟上去。
可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没有默契,分进合流之间发生了不小的混乱,互相碰撞拥挤,一度与前头的两位要员拉开了距离。于谦趁机追到队尾,他身材不高,只能看到那顶高丽冠与黄绸轿顶在视野里逐渐升高,徐徐走到玄津桥的最高处。
突然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,像毒蛇的牙齿一样狠狠钉在他心脏上。于谦的耳边,蓦然响起吴定缘那淡淡的声音:“今天,可还没过完呢。”
于谦一咬牙,把袍角一拎,骤然加速,瞬间超过了三、四个押后的护卫,同时大喊:“快退!快退!”距离最近的卫兵一见有人闯阵,第一时间拦腰合抱,几下扭打便把这个小小文官按在身下。
于谦动弹不得,可那副大嗓门却堵不住,“快退”二字的声量从石狮子旁一直传到玄津桥顶。三保太监听到声音,只是微微回了一下头,继续向前。而他旁边那顶黄绸阔轿的轿帘,却兀然被一只手掀开。
朱瞻基探出头来,惊疑地朝后头望去。这个声音他记得,是那个锦衣卫里的小行人,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?
太子掀帘,轿夫们连忙停下脚步。这一停顿,让轿子与郑和之间拉出了半匹马的距离。郑和勒住马头,正要催促轿夫们快走,鼻子却突兀地捕捉到空气中一丝奇怪的味道。
这味道在他漫长的航海生涯中时时能够闻到,每一次都与战场密切相关,而刚才在东水关码头,也弥漫着同样的味道。
三保太监的反应极快,他一勒缰绳,坐骑扬起后蹄对轿子高高踢去。那匹青海大马生得极为剽悍,钉了铁掌的漆黑巨蹄像一具攻城槌,狠狠撞在轿子顶边的蝠形铜角之上。轿夫们四散摔开,巨大的冲击力推着轿厢,顺着倾斜的石面仓惶滚落下去。
与此同时,从桥下传来一声闷闷的爆破声。整座石桥震颤了一下,从最中间裂开一条大缝。裂缝迅速扩成沟隙,沟隙又变成深壑,很快整座桥面便分崩离析。散开的石块化为无数张裂开的大嘴,裹挟着三保太监连同那头坐骑落入秦淮河中,溅起巨大的水花。
第三章
这一突然的变故,让玄津桥下的人全都呆住了。
这支队伍里只有三分之一是训练有素的守备衙门亲兵,他们第一反应是登桥去营救主官;而其他三分之二都是拼凑而来的鼓吹手、仪仗、门班、轿伞夫子与跑腿小厮。他们惊叫着四散奔逃,想要尽快远离。每个人的行进方向截然不同,两尊石狮子之间的三条通道登时陷入混乱。
于谦奋力一挣,甩开失神的士兵,直直冲到那顶摔倒在桥阶之下的轿厢前。没想到他还没出手拖拽,朱瞻基自己已经挣扎着爬了出来,攒眉凶目,眼神里涌现出腾腾杀气。
朱瞻基不是那种自幼长于深宫的纤弱皇子,他曾随祖父讨伐北元,骨子里深藏着悍勇之气。短短一个时辰不到,居然遭遇两次袭击,还是发生在大明腹心之地。这种突破极限的冒犯,反而把朱瞻基的脾气给逼出来了。
他先踹翻一个蹲在地上不停号叫的旗手,然后厉声喝道:“先下水救人!”亲兵们如梦初醒,纷纷解下甲胄、抛下兵刃,扑通扑通跳下水去捞郑和。
旁边于谦也赶紧放开嗓门,以太子的名义喝令闲杂人等各安其位。他的音量可比朱瞻基高多了,如洪钟大吕,鼓荡耳膜,指挥着那团不安人群逐次后退,让空间让出来。桥头——如今得称为断桥了——的局面,总算慢慢恢复了秩序。
在秦淮水下的营救很快便有了成果,一披猩红大氅从水中被凫水的亲兵们托起来。队伍里有个医官,过去迅速检查了一下,发现郑和的呼吸尚在,身躯也没有什么明显损伤。不过他大概骤然受到冲击,双目紧闭,一时还不能回应呼唤。
于谦并未因郑和的得救而精神松懈,他紧张地护在朱瞻基身前,眼睛却盯着玄津断桥的残骸,似乎在寻找什么线索。
洪武爷入主金陵之时,元寇未靖,因此在各处城门、瓮城、内外高墙以及要路津桥挖了不少藏兵洞。在这座玄津三拱石桥下,工匠们别出心裁,利用拱弓结构巧妙地做出一个极为隐蔽的桥洞。后来大明定鼎,藏兵洞用不着了,慢慢被封堵废弃。
很显然,炸桥的火药,肯定是被堆在这个桥下的藏兵洞里。也幸亏是埋藏此处,水气浓郁,导致火药受潮,炸了个半哑,只是震塌了石桥结构。倘若完全爆发出来,只怕三保太监和周围所有人都尸骨无存。
可有一件事于谦却想不通。
宝船行进的路线以及时间都是规划好的,反贼可以提前做好安排。而太子何时经过玄津桥根本没法预测,那么多火药他们怎么提前准备?
除非……
除非这是一个早早算定的后手。只要南京有高官侥幸在宝船爆炸中幸存,他们一定会迅速进入皇城,而玄津桥是必经之路。在这里提前安排下一招补棋,可以确保打击到漏网之鱼。
这些袭击者的布局,竟然缜密到了这个地步,真是无比坚决的杀意啊!
于谦强抑心惊,很快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一招补棋固然精妙,可无法预测发动时间,因此必须得有人猫在桥下藏兵洞,随时发现目标抵达,随时点火。也就是说,刚才那一场爆炸,肯定得有一个点火者看见队伍经过,这才匆忙点燃,他肯定还在左近!
于谦“唰”地抬起头,眼神一遍一遍地扫过河面。他很快发现,距离玄津桥右侧五六十步开外的秦淮河面,似乎有一个黑点一沉一浮。于谦眯眼再看仔细,那应该是一个人顺着水流,奋力朝远处游去。
“贼人在那边!快!”
于谦急切地唤来几个亲兵,让他们迅速沿着秦淮河岸去追赶。朱瞻基听到于谦的叫喊,也朝那边望了一眼。他绷着脸,先伸出拇指比了一下远近,俯身从地上捡起一把不知谁掉的开元弓,再从一个护卫的撒袋里拈出一支长箭,搭弓拉圆。
他的姿态,是标准的军中挽弓之法。弓弦一响,长箭刺破虚空,如流星般朝那黑点疾飞而去。可惜准头略差,与黑点的脑袋差了半分,没入前方的水中。朱瞻基眼中杀意更加盎然,再拈出一支箭来瞄准。
于谦忙提醒说殿下要留个活口。可惜他话刚出口,弓弦又响。这一箭带着满腔委屈与怒意,越过秦淮水面,正正钉在那黑点的后心。那人的前胸骤然朝前一顶,双手挣扎了两下,整个人朝河里缓缓沉去。早已冲去河岸的亲兵们迅速伸去长竿长耙,连拖带拽把他弄上岸来。
于谦三步并两步赶了过来,只见那支箭镞从后心贯穿了右侧胸膛,令他当场气绝身亡。这箭法着实了得,可也着实可惜。要知道,这可能是他们所能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。
死者是个约摸二十多岁的男子,头梳小髻,用阔边深网罩着,一身青布衫裤,足蹬趿靴,与寻常南京百姓并不无同。于谦搜遍全身,除了一套火镰之外并无任何物品。他不甘心地撕开死者的衣襟,赫然发现在左臂腋窝处,居然文着一朵白莲花。莲花分做三瓣,形似焰团聚拢。
“白莲教?!”于谦双眼骇然睁大。
这三个字,是朝廷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。它兴于宋代,教义宣称弥勒降世,将以白莲化为业火净世,动辄煽众闹事,绵延数百年。从宋至元再到大明,历朝都极力打压封杀,偏偏此教在民间香火极盛,屡禁不止。
最近的一次是在永乐十八年,白莲教众在山东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叛乱,太宗费了好大力气才镇压下去,可见其坚韧与难缠。
白莲教和朝廷之间,可以说是仇深似海。倘若是他们所为,倒能解释这种要置太子百官于死地的疯狂。
这时朱瞻基也来到尸身旁,沉声问道:“这人是谁?可看出些端倪?”于谦一指那文身,压低了声音约略一说。朱瞻基倒吸一口凉气,他久闻这个邪教的大名,不由得头皮微微发麻:“这些事……都是他们干的?”
“如今形势不明,一切皆有可能。”于谦看看左右,有些焦虑。眼下不知道哪个角落里还藏着白莲教的疯子,多在外头停留一刻,就多一分危险。他催促道:“这伙贼人所图极大,必然还有后续手段。还请殿下迅速返回皇城,重聚人心。”
朱瞻基苦笑一声。重聚人心?他的东宫班底,已化为齑粉;他在留都可以信任的两大山岳之镇,一个李隆一个郑和,如今皆身负重伤不能视事。转瞬之间,偌大的一个金陵城危机四伏,而朱瞻基却孤立无援,再无一个相熟之人可用。站在潺潺流动的秦淮河边,堂堂大明皇太子一时间竟有些茫然无措。
这种事情,于谦是帮不上忙的。他只能吩咐几个亲兵收起那个教徒的尸身,送去最近的义舍备查,然后把朱瞻基拽回到玄津桥头。
如今这桥只剩下两岸的桥基断茬,微微上翘,像两节被折断的指骨,彻底无法通行。玄津桥是进皇城的必经之路,它一断,要么北上至竹桥,要么南返到白虎桥,都得绕一个大圈子。
可这种局势之下,谁又能保证,那两处桥下没有埋伏着杀招呢?就算两桥无事,沿途呢?这一带商铺酒楼民居林立,想藏上十几个杀手太容易了。
于谦考量再三,认为最好的选择是留在原地,等候其他有力官员前来救援。只是现在整个南京级别稍微高一点的官员,都在东水关被炸得生死不知,找谁来需要费些思量。
这时一个郑和的亲兵提醒说,刚出事那会儿,三保太监便第一时间传信皇城,命令皇城守备朱卜花紧闭城门,防止贼人偷袭,他应该安然无恙。
朱瞻基闻言眼睛一亮,这个朱卜花他知道,是京城御马监的提督太监,年初刚从京城调来金陵,还带来一支叫勇士营的禁军队伍,负责守备南京皇城。
这支队伍和别的禁军不太一样,它建于永乐年间,主要成员是从草原逃回的青壮汉民男子,所以个个骑术精湛。洪熙皇帝把这支队伍安排给太子做心腹,可见花了不少心思。
宝船爆炸时,朱卜花在皇城留守,未受波及。于是朱瞻基当场手书一封,着人迅速送去皇城,让朱卜花带禁军前来接应。
亲兵领命而去。于谦仍不放心,指挥着其他人分散开来,以桥头为圆心,把守御区域扩散到百步开外的临街铺子。他还派了几个手脚矫健的,爬上附近的房顶高处,防备可能的弓弩袭击。
于谦虽然只是个小行人,可分派调度有条不紊,又借着太子这张虎皮,无论护卫、锦衣卫还是轿夫、号手皆凛然听命。一会儿功夫,桥头便建起一个密不透风的步障区域。现在除非白莲教调来铁骑冲阵,否则绝难威胁到太子。
喧嚣渐渐平息下来,附近店铺里的百姓纷纷冒出头来,好奇地朝这边观望过来。朱瞻基不想让他们见到自己的狼狈样,跌跌撞撞走在两座石狮子之间的桥阶上坐下,眼神活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。
于谦安排停当,走到太子面前,还未及禀告,朱瞻基忽地抬头问道:“你是如何知道,白莲教会在玄津桥上设下埋伏?”他还记得这个小官临上桥的一声呐喊,让自己迟疑了半分,否则落水的可不止是三保太监了。
于谦从怀里摸出一张信纸,恭敬递过去:“殿下离开锦衣卫后,臣得到消息,得知城中可能藏有贼人暗桩,恐有碍于殿下,故而追上来提醒。又怕宫禁森严,故备了一封书信请人传递,只是没想到……”
朱瞻基展信扫了一眼,心头一热。虽然百官尽职乃是本分,可一个小小行人能做到这地步,真可谓是忠纯之臣了。
“以你之见,接下来该如何?”太子不知不觉,已把这八品小官当成了咨议谋臣。
于谦道:“这一次祸极熏天,枝干断折,实是开国未有之局面。臣以为当务之急,是派遣得力心腹,着手追查。须知贼人筹谋极为周备,倘若稍有延滞不决,只怕再无机会找到真相。”
于谦当初急着催促锦衣卫办案,就是怕稍晚一步,很多线索便湮灭无痕了。
朱瞻基摇摇头。第一件事,他心里还有点谱儿,可派心腹查案?自己如今是孤家寡人,哪里还有什么心腹?于谦知道他的难处,连忙开解道:“殿下莫愁,五军都督府、南京守备衙门、五城兵马司、应天府、锦衣卫都有熟习缉事的老手,皆可阶下听用。”朱瞻基沉默半晌,从牙缝里迸出四个字来:“我信不过。”
于谦先是一怔,旋即明白。
不怪太子惊弓之鸟。白莲教既然能渗透宝船运入火药、能买通留守左卫的旗兵巡河灭口、能在与皇城近在咫尺的玄津桥上设伏,谁能保证他们在官府里没有内应?事实上,白莲教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,就是总有信徒在官府里做内应,其中不乏高官大吏。
如今在这南京城里,恐怕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与白莲教无关。
一面是惊天大案,亟需彻查;一面是满城嫌疑,无可信者。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,隔着潺潺流动的秦淮河水望向皇城。
此时虽然已过午时,日头抛洒下来的热力却丝毫不减,朱红边墙上那一溜琉璃叠瓦被映得流光溢彩,煊赫夺目,透着通天的雍容气势。只是光亮越盛,对比越强,在鳞次栉比的巷道桥楼之间,一条条阳光难至的阴影之地格外醒目,它们深深嵌入都城肌理之中,勾勒出一片难以言喻的恶意。
不过在宫墙的边缘,尚还有一条灰边,这里恰在明暗过渡之间,非黑非白,颇为暧昧。于谦凝望远方,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人影:“臣保举一人,堪当此任。”
“嗯?”太子眉头一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