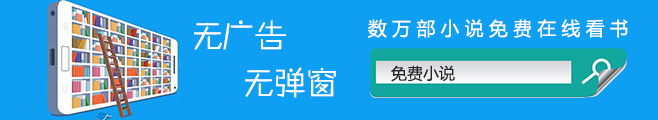红楼之挽天倾 第1753节
贾珩沉声道:“蔡将军,你领兵六千骑,拿下东昌府,护卫我军粮道,不得有误。”
因为哪怕是河南巡抚,但没有内阁和军机处的旨意,也不能擅动兵丁,幸在贾珩的动作十分快,派使者吩咐史鼎领兵前往山东驰援。
穆胜却不以为意,沉吟片刻,道:“济南府城没有多远了,你在此分兵围攻城池,我亲自领兵驰援济南府城,不能让济南府城大破。”
不大一会儿,身着二品武将官服的蔡权以及杜封、肖林等人身披甲胄,快速赶来,面色恭谨,抱拳道:“末将见过节帅。”
“将信传出去,让陈渊公子撤兵,派人突围。”李延庆浓眉之下,坚毅目光现出一抹思索,忽而当机立断说道。
李延庆所率兵丁不多,其本部马队只有三千,原本就是流寇响马,自然多是骑军马队。
陈渊道:“北方最近倒是没有多少军情传来。”
山东,曹州府
青灰色的府城城墙上,鲜血血迹尚在,城门楼上旗帜冒着浓浓硝烟,而不少红色号服,外着黑甲的汉军手持军械,往来其间。
而此刻,李延庆立身在城头上,眺望远处的登莱水师,面上现出凝重之色,问着一旁的副将郝从远,问道:“城中还有多少粮秣,可供支应几天?”
只是一座县城,城池并没有那般高,倒也用不上什么大型的攻城器具。
陈渊道:“如今出兵时机千载难逢,去年西北之战,朝廷损失惨重,又连经大战,国库渐渐见底,如果让汉廷再摆平了内部乱局,彼时,以汉廷的国力,以那贾珩小儿的手段,辽东破灭只是时间问题。”
陈潇点了点头,也不多说其他。
康鸿又吩咐说道:“仔细拷问附逆贼人,将城中与白莲教勾结的凶逆一并捉拿。”
豪格浓眉之下,那双凶戾之芒充斥的虎目目光灼灼,沉声道:“再打下去,各路的援兵都到了山东,几路夹攻,我们无路可逃,该想下一步进兵方略了。”
忠靖侯史鼎沉声道:“仔细甄别城中的白莲妖人,凡有委身侍敌者,一律以附逆罪名,就地正法!”
豪格面色阴晦不定,道:“本王这就派人去向盛京传信催促。”
其实,陈渊对这位女真肃亲王的颐指气使,有些心头不满,但一直暗暗忍耐着。
豪格说着,岔开话题问道:“等李延庆那边儿怎么样了?能否挡住登莱的援兵?”
肖林面色一肃,拱手称是。
而那两扇铜钉剥落的朱红城门已经大开,不少兵丁冲入进去,喊杀声在城中不时响起。
山东,章丘县
原本济南府城被围攻之时,这座巍峨高立的县城,也被陈渊分兵掠下,劫掠其中粮秣以供应大军所需,故而李延庆率领骑军阻击登莱援兵不敌,就一路节节败退至章丘县城,打算借助县城的城防,抵挡登莱的水师兵马。
詹东进就有些招架不住,毕竟济南府卫的卫所再是被洗脑,但作训水平以及军事技能,军纪严明,又远非康鸿手下的河北边军可比。
汉军这次虽然驰援而来,但攻城器械倒也准备的周全,此刻兵马全军押上,攻势十分迅猛,如潮水一般源源不断。
……
如今攻打济南府城不利,陈渊已是负面情绪爆棚,只觉宏图大业都将成饼。
陈渊自也察觉到形势的变化,心头就有些沮丧莫名。
而原卫指挥佥事,也是白莲教的堂主詹东进,沉吟片刻,说道:“丁壮上城,协同守御,另外,将那两门佛郎机炮抬过来,阻挡官军攻势。”
随着战鼓“咚咚”响起,鼓声几乎密如雨点,大批兵马开始向着武定府城如潮水般涌来。
不得不说,豪格的这个方略颇有一些可行性,效仿太平天国以及李闯的流寇手段,祸乱几省。
自中午一直到傍晚时分,残阳如血,晚霞烂漫,而青砖与条石垒砌而立的城墙之下尸相枕籍,鲜血顿时浸染了土壤。
豪格道:“虽然兵马会少,但只要运作得当,汉廷只能疲于奔命。”
……
郝从远面色凝重道:“最多只能支撑三天。”
家将穆晨并辔而行,在一旁挽着一根马缰绳,看了一眼城头上迎风飘扬的旗帜,目光凝重几许,说道:“世子,叛军和白莲教匪想要借城拒守。”
“城中乏粮,最多还能再支应三五天,正是将破城之时,不若再坚持两天。”陈渊目光冷然,有些不甘心说道。
陈渊心底就有些不甘心,沉吟道:“王爷的意思是?”
两人一起用着午饭。
大批军士执兵向着城头冲杀,没有多久,就传来“叮叮铛铛”之声,以及刀刃入肉的“噗呲”之声。
杜封面色坚定,拱手称是。
经过河南都司兵马三万人,近一天不计代价的攻防之后,曹州府州也终于插上了一面刺绣着“汉”字的旗帜,随风飘扬,猎猎作响。
“盛京的王公贵族不是傻子,前些时日就有动向,静待北疆消息就是,原本是在济南府城攻陷以后,再从北方入关。”豪格皱了皱眉,心头就有几许不快涌起。
“大哥,朝廷的兵马分兵了。”这会儿,另外一个方脸盘,络腮胡的大汉,沉声道。
说来也巧,就在豪格与陈渊议论之时,一个身形魁梧,颌下蓄着短须的军将,快马而来,抱拳道:“王爷,李将军派人说,登莱方面的驰援兵马不少,李将军言兵力不足,最多能够抵挡一两日。”
大势已去,事不可为,此刻只有八个字在豪格心头盘桓。
贾珩说着,又将冷眸投向杜封、肖林,说道:“杜将军,你领兵八千前往兖州府,光复兖州城。”
此外,就还有一些山东卫所叛军方面的骑军抽调出来归其指挥,抵挡登莱方面,是故两厢叠加而论,六七千…故而,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轻骑,其实是没有太多问题的。
白莲教在齐鲁之地积蓄势力已久,如今好不容易发动一场大事,但只是因为济南府城攻城不顺,从此尽作流水,却要转战南北,冒着被围剿的风险。
豪格见此,道:“那就只能在山东被贾珩小儿的兵马围攻而死。”
但如今内应事败,自然万事皆休。
贾珩转眸看向一旁的肖林,道:“肖将军,泰安府乃为济南府退兵必将之所,你率兵一万,前往泰安府城,截断济南府城兵马的归路,断其粮道。”
这时,副将唐相朗声道:“大人,卫国公的兵马已经到了,大人是约定进兵,还是再一同进兵?”
可以说,兄长保龄侯史鼐的阵亡,让这位武侯心头可谓愤懑到了极致。
其实,陈渊所言倒是旁观者清,自平安州大捷以后,大汉国力的确是虚弱了许多,国库空虚,京营将校士卒也有一定的厌战情绪。
而这再有两天的路程就能接近济南府城,这一路贾珩率领兵马,同样是狂飙突进。
穆晨点了点头,吩咐着身旁的裨将,道:“准备攻城器械,即刻攻城!”
……
城中有百姓受白莲教蛊惑,那么同样也有一些忠臣义士拳拳之心,心向朝廷。
史鼎转而又吩咐着,冷声道:“着人搜集城中府库粮秣、金银购置粮食,支应大军。”
河南都司出兵同样仓促不已,不少兵马开赴曹州,但实际的粮秣和辎重还在后方府县转运,主要是迅速收回曹州府城,扑灭山东的叛乱局势。
而从中抽调的步卒以及登莱府卫的骑军,兵力合计也有七八千,李延庆拼凑而来的骑军骤然遇敌,根本抵挡不住。
……
毕竟也是武将世家出身,显然也明了其中用意。
蔡权面色一肃,拱手说道:“是,节帅。”
忠靖侯史鼎同样已经收复了曹州府城,此刻这位武侯,身上穿着孝服,面容颇有几许悲怆。
济南府城
经过两天两夜的不间断攻城,这座栉风沐雨,巍峨高立的府城虽然残破了许多,但依然安若磐石,岿然不动。
而武定府城城头上,军士和丁壮来往巡弋,几是如临大敌。
事实上,在历史上清军入关以后的“济南之屠”中,十万清军攻打只有几千人守卫的济南府城,就打了整整六十天才破城,在没有火药的冷兵器时代,攻城本来就没有那般容易。
陈渊道:“江苏之地,仍有朝廷重兵屯驻江北大营以及江南大营,单靠我们这些人马,也逃不过围剿,这样时间一长,只会兵马越来越少。”
而随着时间过去,此刻蔡权、杜封、肖林等人,率领兵马也先后前往几座府城,开始陆陆续续收复城池。
而此刻,河北保定的兵马已经先一步抵达武定府,领兵之人乃是河北提督军务总兵官康鸿。
原武定府衙,官署已经为河北边军占据,前后几重进衙门,放眼望去,都是身着红色号服,外间披一身甲胄的兵丁,手执一把长刀,脸上仍还残留着厮杀之后的猎猎煞气。
至于此刻,济南府城攻防战彻底失败,陈渊以及白莲教都将彻底收缩,等待官军的剿捕。
康鸿皱了皱眉,落座在条案后的椅子上,说道:“清点府库,将粮秣归集一起,稍后就前往济南。”
副将叶惟亨拱手称是。
贾珩点了点头,说道:“陈渊与豪格两人,最近应该会往泰安府,兖州府跑,派人封堵一手,阻遏他们的去路。”
陈渊深深吸了一口气,压下心头不停翻涌的怒火,说道:“王爷,我们先往兖州府和泰安府,两地都留驻有重兵,且地势险要,可与官军相持,王爷可给盛京的摄政王写信,全面发兵进略蓟镇,以接应山东局势。”
“杀!!!”
郝从远应了一声,然后吩咐着人送信去了。
事实上,金陵作为陈汉故都,久不历战事,江南江北大营如果是没有经过贾珩的整饬和作训,那还有成事之机。
那锦衣府卫李述闻言,抱拳称是,然后,就前去寻蔡权等将。
贾珩面色微定,道:“先吃饭吧。”
官军行军尚有粮秣供应,而叛军同样不是不吃不喝的机器人,也需要搜集粮秣供应大军。
官军快马驰援,白莲教也不可能扔下一座府城不要,进行所谓的化整为零,事实上也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。
当初,隆治年间,汉军在辽东的这场大败让陈汉元气大伤,而康鸿作为亲历者,一听女真的礼亲王豪格也在叛军之中,自然心有忌惮。
城外,中军大帐,陈渊以及豪格手下的兵马渐渐回城。
陈潇叮嘱道:“倒也不可小觑。”
“侯爷,城中叛军已经被彻底肃清。”这时,史家的家将史和,昂首阔步,进入官署之中,朝着忠靖侯史鼎抱拳说道。
“我们先一步攻打济南府,方才听将校说,围攻济南府的叛军兵力也不多。”副将叶惟亨压低了声音道。
此刻,东平郡王世子穆胜,已然领着登莱的兵马,浩浩荡荡前来,骑步两军打着旗帜,遮天蔽日,似是一眼望不到头。
尤其是先前,陈渊数次提醒豪格,让其发动盛京以及朝鲜的兵马,配合山东方面的行动。
豪格闻言,道:“去年已经遭过一场大败,现在盛京也调拨不出太多兵马了,而且汉人火器犀利,难以进兵。”
豪格此刻心头涌起一股无力感,看向一旁的陈渊,说道:“这城池攻破不下了,已无机会。”
这会儿,军士已经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,行至近前。
“以我之意,携兵丁入江苏,乱其财赋重地,而后转战安徽,效流寇手段,搅乱汉廷。”豪格浓眉之下,目光咄咄而闪,低声道。
因此,整个崇平十七年原本是准备休养生息,励精图治,可山东乱局突然,根本没有给陈汉官员太多的机会。
陈渊以略有些抱怨的语气,说道:“王爷先前在局势大好之时,就该让盛京方面出兵北方,那时,朝廷不愿议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