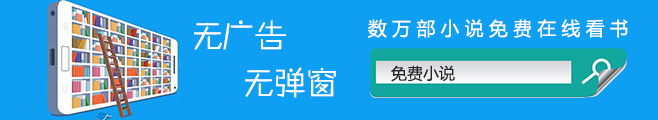红楼之挽天倾 第836节
几人说着,来到坤宁宫,此刻暮色自天穹泻落,殿里殿外有宫女点着灯笼,轩敞、奢丽的殿宇顿时明亮起来。
端容贵妃从绣墩上起身,见宋皇后身旁并无旁人,问道:“姐姐,陛下还在内书房批阅奏疏?”
“陛下说一会儿就过来。”宋皇后玉面之上笑意凝滞些许,道:“我们先坐下叙话。”
“明天的事儿,姐姐都准备好了吧?”端容贵妃问道。
宋皇后轻声道:“已经准备好了,太后那边儿其实还是想回洛阳一趟,老人家一直心心念念许久了,这次韩国太夫人领着几个诰命还有冯家的人过来,更是让太后心头生出了几分动身”
端容贵妃柔声道:“先前河南那边儿生了乱子,现在变乱初定,倒也能过探探亲,只是许多年过去,物是人非,说来,我与姐姐也有许多年没回过洛阳了。”
听容妃提及家乡,宋皇后美眸现出一丝缅怀,柔声说着。“再看看陛下的意思吧,陛下这两年也有前往洛阳之意,关中这几年冬天冷、夏天热,陛下近年也有巡幸洛阳之意。”
贾珩心头却是微动,思忖着崇平帝的心思,其实,在督豫之时,洛阳、开封两地都有行宫。
在隆治年间,太上皇喜欢到处巡幸,在洛阳、开封、金陵都有巡幸,让太子留守神京。
而在洛阳、金陵一中一南两京之地,待上几个月处理政务都是家常便饭,也不全都是贪图享乐,隆治帝前面二十多年,文治武功都是可以称道的,甚至可以说是隆治盛世。
而崇平帝荣登大宝之后,已经十多年都待在神京城,是不想去吗?倒也不是,太上皇就在神都荣养,崇平帝可以说是哪儿都不敢去,谁知道回来之时,神京会不会城头变幻大王旗?
当然也不会让太上皇再去金陵,相当于父子两人都耗在了神京,当然出去不出去也没什么不同。
但这种势必不能长久,国朝立国百年,经过太宗、隆治两代帝王的巡幸制度,没有天子不得出京的规矩,只是太宗俭朴,巡幸都是轻车简从,带着政治目的,而隆治奢华,排场重大,游山玩水,江湖猎艳那是都不耽误。
故而,如果有机会,崇平帝肯定要巡幸金陵,对错综复杂的江南官场进行整饬。
但这一切……或许要等太上皇驾崩之后了,而这几年关中夏热冬冷,只怕经过恭陵坍塌一事的太上皇,真没两年好活了。
贾珩目光闪了闪,不怀好意想着。
这时,宋皇后看向正在与贾珩轻声说话的咸宁公主,道:“止儿,太后是怎么说的?”
咸宁公主转眸过来,清绝姝丽的容颜上见着思索,声音如冰雪融化,清澈明净,道:“太后说国家近年多事,不要大操大办,铺张浪费的。”
宋皇后点了点头,雪肤玉颜上见着浅浅笑意,说道:“但也不能失了天家体面,难一些,苦一些,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担着就是了。”
婆婆说是那般说,但这个生日还是要好好张罗一番才是。
第687章 甄晴:她真真是魔怔了,都怨那个混蛋!
坤宁宫
夜色降临大地,夏夜暖风吹动帷幔,殿中热气融融,一座鹤形宫灯之畔烛火摇曳,明灭不停,将几道人影投映在通明如水的地板上。
宋皇后提及太后,旋即看向贾珩,轻声说道:“太后先前点名要见你,明天你也过来长乐宫。”
贾珩轻声道:“先前圣上已经叮嘱过臣,臣明日再前往宫中。”
宋皇后点了点头,笑了笑,安慰说道:“你也不用担心,太后她老人家慈眉善目的,你见过就知道了。”
眼前的少年,说来,对冯家也不错,说来还是因为冯家的人进京在太后跟前儿提起贾子玉,然后太后原本对其已有家室,还能尚配咸宁的一丝不乐意,也没有了。
咸宁公主眨了眨清眸,低声笑道:“先生与太后的关系,说来比我还要亲近一些呢。”
相比姑姑在太后那里,她终究还要隔着一代。
贾珩闻言,心头一跳,如何不知咸宁是在说晋阳长公主,凝眸瞥了一眼咸宁,使以眼色,心道,这话如何好乱说?这要是让宋皇后与端容贵妃怀疑起来,还能得了?
宋皇后见着“挤眉弄眼”的两人,心头也有几分好笑,这些小儿女之间情投意合,的确看着
这用后世话说,就是见着两个小两口恩爱甜蜜,脸上时不时露出姨母笑,而宋皇后自是咸宁公主的姨母。
听贾珩叙不日启程扬州,咸宁公主轻声说道:“先生,什么时候走?
贾珩低声道:“嗯,也就这几天,锦衣府已经在准备好了车马,再将京中的事交代一番后就走。”
咸宁公主明眸熠熠地看向贾珩,低声道:“等先生那边儿顺遂一些,可要给我写信才是,别忘了。”
显然也担心贾珩将自己抛在脑后。
贾珩轻声应允下来。
咸宁现在变得有些黏人,或者说与他定情之后,恨不得与他永远黏在一起。
端容贵妃瞧了一眼小两口在低声对话,秀眉凝了凝,轻声道:“子玉要南下扬州了?”
贾珩不欲深谈,随口岔开话题说道:“圣上交办的差事,不日启程。”
端容贵妃想了想,看向那蟒服少年,道:“那子玉在外一切以小心为要。”
大抵是岳母对女婿的关切。
“臣会谨记娘娘教诲。”贾珩连忙道谢。
“母后,母妃,五姐。”就在几人叙话之时,忽地,从远处跑了一个小童,正是八皇子陈泽,在内监的陪同下,说说笑笑地来到殿中,向着宋皇后、端容贵妃行礼,然后看向一旁坐着的贾珩,笑道:“五姐夫,你也过来了。”
“泽儿。”端容贵妃在一旁板着脸,神色凝霜,道:“没大没小的。”
咸宁公主脸蛋儿羞红成霞,近前,拧着陈泽的耳朵,清眸笑意流波,嗔恼道:“你现在胆肥了,连你姐姐的玩笑,都敢开了。”
“姐姐,别拧,哎幼,疼。”陈泽口中叫着疼,转而喊着宋皇后,求告道:“母后,救泽儿。”
其实论起来,不仅是咸宁还是陈泽,该唤宋皇后一声姨母,而相比端容贵妃对子女的严厉,宋皇后对两个侄女、侄子无疑要温柔宽厚许多。
宋皇后笑道:“咸宁,别欺负你弟弟了,泽儿,你刚才称呼,都是听谁说的?”
“母妃身旁的嬷嬷说的。”陈泽坐下来,近千帆,规规矩矩说道。
端容贵妃柳叶细眉之下,明眸闪烁,隐见几分冷意浮起,这些宫人就是嘴碎,这八字还没有一撇,就开始嚷嚷起来。
宋皇后嫣然轻笑,说道:“这可不能胡乱传着,对你姐姐总归不好。”
陈泽点了点头说道:“母后,儿臣知道了。”
端容贵妃道:“姐姐,这孩子有时候也挺跳脱的,也该正经读几年书了。”
“先前不是说给他找了个老师,现在确定了什么人?”宋皇后凝眸问道。
“找是找了,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陆理陆学士,学识渊博,先前臣妾还想寻着国子监的祭酒刘瑜中,但治学太过古板僵化,再说年龄大了,精力不济,而国子监司业颜宏也挺合适,但陛下否了。”端容贵妃轻声说着,显然对自家儿子的教育十分上心。
贾珩原在下首坐着,闻言,手中的茶盅轻轻一顿,圈圈涟漪在茶水中荡起,心思起伏莫名。
陆理……八皇子的老师怎么能是陆理?
不过稍稍想想,倒也属平常,陆理是状元出身,在翰林院磨勘甚久,学问与文采也十分出众,担任一位幼年皇子的老师,从身份和学问而言,合情合理。
只是这么一个人……
“先生在想什么呢?竟这般出神?”见贾珩停杯思索,咸宁公主凑近脸去,星眸看向对面目光幽深的少年。
贾珩笑了笑,道:“没什么,想起了一桩旧事。”
说着,喝了一口。
虽说魏梁两王都为皇后所出,魏王再不济,还有梁王,但八皇子天资聪颖,难保陆理不会烧冷灶,还需要再观察观察。
这时,咸宁公主也不疑有他,而是看向宋皇后与端容贵妃,柔声道:“母后,母妃,阿弟上次吵着说让我教他骑马、射箭,说是来日大一些,领兵出征东虏,为父皇分忧。”
宋皇后笑道:“还有这么一回事儿?泽儿,你要当大将军啊?”
陈泽清脆的童声带着几分稚嫩,道:“父皇牵挂着战事,天天睡不好吃好的,等儿臣大一些,定要领兵为父皇出征分忧。”
宋皇后听着,轻轻捏了捏陈泽的脸颊,看向端容贵妃,轻声说道:“妹妹,你听听,泽儿这般年纪就有这把孝心了,真是难得了。”
端容贵妃蹙了蹙秀眉,轻声道:“他还小,不知道外面的事儿险恶艰难,等他大一些再看就是了。”
作为母亲,自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,舞刀弄枪,不成样子。
咸宁公主清声道:“从小看一些兵书也挺好的,我看阿弟已经开始寻着一些,平常还让缠着我,让我给他讲先生的三国话本呢。”
宋皇后看向一默然而听的贾珩,笑道:“泽儿如想学行军打仗,可以和子玉学着,子玉你若是得闲的话,也教教泽儿兵策将略。”
陈泽看向贾珩,道:“姐夫在河南威名赫赫,可要教教我才是呀。”
贾珩连忙应道:“如是公务不繁重的话,微臣会的。”
而后,贾珩与咸宁公主低声说着话,听着后妃两人议着一些家长里短,比如谁家的诰命夫人今年又有了孩子,比如哪家宗室之女嫁给了哪一家勋臣的公子,女人聚在一起,就喜欢谈论着这些。
贾珩安静听着,低声与咸宁说着话,不多时,殿外传来一道内监的声音,“陛下驾到!”
殿中众人都相继停了谈笑,纷纷起身朝殿外迎去,向着崇平帝行礼。
崇平帝大步而来,看向众人,冷硬的面容上见着笑意,说道:“都免礼吧。”
在宋皇后的相迎下,拉着崇平帝坐在软榻上,笑道:“陛下,臣妾让宫人准备膳食。”
崇平帝点了点头,道:“这天挺热的,说来也没什么胃口。”
说着,看向贾珩,轻声问道:“子玉先前建言趁着大旱之时,营修水利,如今北地官员兴修水利的奏疏,倒是没少上,想来今年秋粮会有一些好收成了。”
因贾珩在中原,江淮营堤造堰,抗洪备汛得了彩头,再加上先前崇平帝就督促地方官府谨修水利,故而现在的北方官员都兴起了一股兴修水利的风潮。
贾珩沉吟片刻,似欲言又止。
崇平帝笑道:“子玉有话不妨直言。”
贾珩道:“圣上,就怕地方官员,以此邀功,广兴土木,摊派徭役,使百姓苦于河工,多生怨言。”
“哦?”崇平帝脸上笑意凝了下,正色问道,显然为贾珩的“前后矛盾”之言有些不解,当初提议大修水利的是你,为此还上了《陈河事疏》,现在又说河工可使百姓被徭役之苦,于上生怨。
贾珩道:“圣上,兴修水利,以备旱洪两灾,自是应行之事,然圣上,上有所好,下必从焉,地方官员以圣上重视农耕水利尤甚,故着眼于政绩之虑,不乏官员不经慎思,在辖域大兴土木,广发百姓,可能当地原不适凿引水渠,偏偏因官员逢迎于上,河徭之风,愈演愈炽,摊派徭役,强募民财,百姓怨声载道。”
崇平帝闻言,面色凝重,思忖着一种可能。
如果旁人这般说,自是心头不悦,但贾珩这位曾经大力陈说水利营造必要的臣子,并且以中原、江淮之地前例证明了“水利兴则稼穑兴”的道理。
那么这番“改弦更张”之言,自是引得这位天子深思。
贾珩道:“是故,臣以为,自府一级筹拨钱粮兴修水利,应向工部都水司监呈报,由水利官员赴地方查证有务必要,同时地方督抚官员也要检视兴修水利堤堰之利弊,而且不得向百姓摊派徭役,不得强制募捐,同时将其列入都察院巡查地方之事项。”
大型工程上马之前,势必要进行评估、论证,而北地的地方官员,很可能为了政绩,在地方大搞重复建设,无效建设,折腾百姓,举债……嗯,这时候还没有这个模式。
这就是秉黄老之学的官员所言,与民休息,轻徭薄赋之缘由,不胡乱折腾,因势利导,系统还能自动平稳运行,一起了雄心壮志,就容易不切实际。
只要不折腾老百姓,百姓自己就会发展起来,不管是小农经济,还是商品经济,都会渐渐繁荣起来,即所谓自由经济理论。
很多时候,真是一动不如一静。
这般一来,肯定能把一些假朝廷重视农耕水利之名,而行搜刮财货的贪酷之吏心存疑虑,大浪淘沙,留下的就是愿意做实事的能臣干吏。
正因为一管就死,一放就乱,所以才要拿捏一个火候。